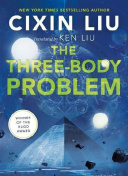改变命运,从一间农家小院开始
1993年8月8日,在贵州省一座简陋的农家小院里,36名学生开启了兴农中学的第一课。这个三层楼高的小院,是校长蒲邦顺向学生家长借用的,来上课的学生,则全部是附近村庄的中考落榜生。他们的教室是堂屋,操场是山坡,宿舍漏风又漏雨,但每个人都满怀期冀——期冀着从这里开始,走向不同的人生。
31年过去,兴农中学成为贵州省办学规模最大的非营利性民办高中之一。近日,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走进兴农中学,听学生、老师讲述他们与兴农的故事。
 1993年,兴农中学在一间农家院里成立。(采访对象供图)
1993年,兴农中学在一间农家院里成立。(采访对象供图)
一个“跳农门”的时代
得知自己中考落榜时,杨连富的泪水忍不住涌上眼眶。
和村里的大多数孩子一样,小学和初中,杨连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务农,十点半赶去上课,下午三点放学后再去放牛、砍柴。在忙碌的劳作外,他唯一的梦想便是能够考上一所中专,走出大山。
“那是1993年,是我们想靠学习跳出‘农’门、改变命运的时代。”兴农中学第一届学生杨连富说,“那时中专是我们的首选。我从没有想过读高中,也读不起。”
参加中考时,杨连富第一次从家中翻出了户口本。他父母走得早,从小便由乡亲轮流抚养长大,直到中考报名时,杨连富才知道父母为自己登记的名字叫“杨老五”——代表他是家中第五个孩子。
“我努力了很久,把所有梦想都放在考中专上。知道没有考上的瞬间,我的眼泪就在眼睛里头。很难过,因为我又要回到毫无希望的生活和劳作中去。”杨连富说。
那时,班里没考上中专的孩子,一部分回了农村,另一部分则选择去外地打工。时值改革开放,沿海城市大量招工,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南下农工潮。16岁的杨连富也觉得“都是干零工,至少那边工资会高一些”,很快,他便收拾好包袱,准备到广东去。
就在杨连富准备出发的前几天,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,他的初中老师急匆匆地敲开了他家的门。
“终于找到你了,你不用去打工了!”老师说,“有个学校今年开办第一届,他们对像你这样的农村贫困孩子不收学费,而且包吃包住,我送你过去。”
听到这句话时,杨连富觉得他的生命里、他的眼前好像突然打开了一扇窗。整整三十一年过去了,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。
“那个瞬间,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。”杨连富说。
理想与雄心
老师口中的这所学校,是刚刚成立的“贵阳市白云区艳山红乡私立兴农职业学校”,也就是后来的贵阳市白云兴农中学。
要称呼此时的兴农为一所“学校”,多少有些差强人意。那时,它只是一个两层半的农家院,只有一间教室,一个中考补习班及班上的36名学生(后来增至43人)。院子里没有自来水,每天早上学生们起床时,老师只能端来一盆水让大家轮流擦擦脸;没有运动场,只能用松木搭在树上捆了作单杠。
“刚开始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”,民进会员,兴农中学党支部书记、校长蒲邦顺说,“但是家长没有埋怨我们,学生也没有埋怨我们,大家都是农村来的,除了想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,没有其他渴求。”
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,英语是最难学的科目。杨连富记得,他们的英语课是从A、B、C开始教的,其他科目则是从初一开始,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他们要补完整个初中的知识。
“下了晚自习后,我们班没有一个学生会自己主动去睡觉。”杨连富说,“如果老师不强制我们休息,我们会学到凌晨两点、三点,早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起来。”
为了把握住来之不易的第二次机会,班上的每个人都在你追我赶。不知不觉中,杨连富就落在了后面。他说:“我很努力,但是我的基础很差。每次考完试看到成绩没有提高,我都会躲起来偷偷地哭泣。”
让他倍感压力的不只是成绩,还有自己的出身。即使这个班里全部都是农村学生,杨连富的家庭条件依然是其中格外差的那一个,无论他怎样努力,都好像摆脱不了成长环境带来的自卑心。
有一天,当杨连富拿到批阅后的考卷,暗暗落泪时,蒲邦顺找到了他。
“只要你有雄心、有志气、肯吃苦,我相信你一定会学好的。”蒲邦顺对他说。在班上,他为杨连富写了一副长长的对联,是清代作家蒲松龄用以自勉的话:有志者,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
“当时的我被这句话里那种雄心和霸气深深地震撼到了”,杨连富说,“从那天开始,我就不会再哭泣。”
1994年中考,兴农中学第一届的43名学生中有42名都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专,还有1人考上了高中。考上中专就意味着有了工作,有了工作就意味着有了收入,放榜时,教室里一片欢呼。这一次,命运也终于没有将杨连富拒之门外。
 2013年8月8日,兴农中学举办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。(采访对象供图)
2013年8月8日,兴农中学举办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。(采访对象供图)
“飞虎队”
第一届学生毕业后,蒲邦顺在荒山下面租下了一栋废弃的三层办公楼,作为兴农中学的新校舍。他也和妻子夏晓霞一起,把家搬进了其中一间小屋。
“一开始条件差,这个屋子也没有卫生间之类的,两年以后我们把两间教室打通,改成了住房,条件稍好一些。”夏晓霞说,“每天能看到学生、听见铃声,心情也挺好。”
屋子一天天变好,学校也一天天热闹起来。首届学生几乎全部跳出“农门”的斐然成绩,让兴农在当地一下出了名,而随着中专地位的下降和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,来到兴农的学生也更多变成了那些考不上好高中、好大学,被其他人称作“问题学生”的青少年。
“可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‘好孩子’,难道其他孩子都应该被废弃吗?”蒲邦顺说。
实际上,在兴农里,不只是学生们不是“好孩子”,这所学校的校长、副校长也曾是“差生”。兴农中学执行校长付恩佑说:“我深刻地体会过‘教育就是唤醒’这句话。”
上高中时,付恩佑和他的舍友们自称为学校里的“飞虎队”——因为每到夜里,他们总是翻墙出去打台球,早上五点前再翻墙回来,这样就不会被查寝的老师抓到。
“飞虎队”的夜间行动,一直持续到高三上学期。“我记得非常清楚,1989年11月18号的晚上,我们整个寝室的人都翻墙出去了”,付恩佑说,“凌晨五点回来的时候,我们的班主任就坐在寝室里面,他看到我们只说了一句话:‘你们回来了,我走了。’”
那一刻,站在宿舍里的所有人都感到羞愧难当。从此,“飞虎队”队员定下了一条规矩——“谁再出去打台球,其他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揍他”。半年后,付恩佑考上了大学,并最终成为一名地理教师。
很多年后,付恩佑在兴农遇到了一位学生,就像从前的他一样,不爱学习、不听老师的话。有一回,他光着膀子走在学校里,付恩佑看到了,便把他叫到面前,问道:“你身材怎么练的?真羡慕你!”
“从那之后他就改变了。”付恩佑说,“在那之前,他一直认为自己‘在所有老师眼里都是人渣,是一无是处的人’,没有人会称赞他。”
“最重要的教育是使一个孩子在人格上不自卑,”蒲邦顺说,“如果你不爱一个学生,没有给他一种同情、一种关怀,你怎么可能教好他?”
独山
在贵州省最南端,距离贵阳市大约170公里的地方,有一个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少数民族自治县——独山县。
曾经的独山县,中学教育水平排在黔南州的倒数之列。2020年以前,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,教育资源不足,好老师纷纷出走其他地区,好学生也纷纷到都匀或贵阳等地求学,一来一回,花销极高。
“刚到学校的时候,我四十多岁,很多人对我说:‘你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可以躺平了。’”独山县兴农中学教师周开霞说。
但在心里,周开霞并不想躺平。她是独山本地人,出身农村,住过一家只有三平米的房子,受过村里人的冷言冷语,经历过、体会过教育的价值,也总是期望独山的教育能有靠自己“翻身”的那一天。
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她一个。2013年,贵阳市委市政府发出了教育扶贫的号召,作为“民办教育之星”的兴农中学接到了自己的任务。时年72岁的蒲邦顺来到当时的独山县民族中学,但是刚到学校没多久,他便拒绝了当地提出的派遣老师辅助教学的方案,而是将所有本地的老师召集起来。
“蒲校长说:‘我相信我们独山的老师,能办好独山的教育。’”周开霞说。回忆起那时的情景,她不禁流下泪来。
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周开霞。在那之前,她从未感受过这样的信任——贫困地区以高薪或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名师、名校长是教育扶贫最常见的方式。在贵州,一位从外面请来的教师年薪可能高达几十万,同时享有住房、子女教育、旅游等各方面的多重优惠,而本地教师的工资往往只有小几千而已。
一时间,台下独山老师们“不要老师!我们要自己干!”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,看到老师们激动的样子,蒲邦顺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:“教育扶贫不应该是派老师去给学生讲点课或者捐点图书,而是要从根本上挖掘出本地教师的潜力。”
不久后,独山县兴农中学成立。改换名字、新建校园,引入了激励机制,并在独山和贵阳两所学校间建立起教师交流的渠道。想要证明自己的老师们立刻投入到教学中,他们有了更多机会去贵阳市内参加培训,去的人回来后再将培训内容讲给其他老师听。就这样,不到三年,这所学校便成了整个州里的佼佼者。
“有一次期末考试,我带的班级拿到了第一名,学校奖励了五百元。”周开霞说,“钱不多,但这是对我们老师的认可,我得到了一份成就感,和一份尊重。”
 2024年开学典礼,蒲邦顺和学生们在一起。(采访对象供图)
2024年开学典礼,蒲邦顺和学生们在一起。(采访对象供图)
改变的和没有改变的
31年过去,曾经的那座荒山,已经由学生和老师亲手栽满了树苗;曾经容纳所有师生的三层小楼,如今只是占地近200亩的校园里一个略显老旧的角落。
蒲邦顺和妻子夏晓霞依然住在这栋楼里,每天伴随着学生们的上课铃声、下课铃声生活,一放假,校园清静了,他们反倒会觉得不习惯。偶尔看着校园,蒲邦顺也会感慨:我们的学校怎么变得这么大了?
小时候,蒲邦顺的父母为了供他读书,想尽了一切办法。1942年,他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,常常背着柴火和米上学,一直读到大学,都是靠着国家的助学金。大学毕业后,为了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,蒲邦顺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书,在新疆待了将近二十年,最终辗转来到贵州。
创立兴农中学时,蒲邦顺已经52岁,那时的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“我在求学的道路上,因经济困难而遇到的种种窘迫情景至今不能忘怀。历尽千辛万苦,我终于读完了大学……而今又办了这所学校。我想用我微薄的力量,扶一把与我的青少年时期有着相同命运的农村孩子。”
1993年,蒲邦顺用三千块钱创办了兴农中学,招收第一届学生时,为了解决农村孩子的学费困难,他号召农民“你们养好猪,我们教好书”,规定可以用农副产品(例如蔬菜等)按照当天最高的市场价格抵交学费。后来,每每有农村孩子找到他,无论交不交得起学费、无论成绩如何,蒲邦顺总是说:“只要你愿意上学,我们就愿意收。”
1997年,兴农已经起步,蒲邦顺看到高中的发展前景,立刻开始申办高中;1998年,他感到高校扩招不再遥远,迅速贷款修建了教学楼;2004年,兴农中学成为贵州省民办教育首个二类示范高中,从此生源暴增;2019年,兴农中学正式登记为一所非营利性民办学校,并延续至今。
这些年里,至少有5个上市教育集团想买下兴农,最高报价达到8个多亿。但是每每跟对方坐在谈判桌上,蒲邦顺总会想:“我只有三千块钱本钱,是学生们建设了兴农中学、发展了兴农中学、成就了兴农中学,如果我把它卖了6个亿、8个亿,那么贵州的老百姓都要骂我。”
如今,蒲邦顺已经82岁,在毕业典礼上送别了无数学生。学校打了几十个青铜鼎,把成立至今的五万多名学生的名字都刻在鼎上,寓意着“我把你的名字刻在鼎上,你把伟大祖国刻在心中”。有的学生半途退学,知道这件事后回来问他“能不能把我的名字也刻在鼎上?”蒲邦顺一一答应,因为“哪怕一个学生考不上大学,也依然可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。”
“即使他们考不了清华北大,但他们是国家真正的建设者、劳动者和保卫者。我们所希望的,是这里的孩子能感受到他没有被社会歧视、没有被社会边缘化,长大以后,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”
近些年,从兴农中学毕业的一部分学生,自发成立了“兴农中学校友爱心接力基金”,帮助尚有困难的学弟学妹顺利完成学业。蒲邦顺说:“他们富而有责、富而有义、富而有爱的情操与担当,令我感动,让我自豪!”(《中国新闻》报 作者 王曦泽)
改变命运,从一间农家小院开始
改变命运,从一间农家小院开始
爱情不设限
 78%好评(76人)
78%好评(76人)
 70
70





- 软件大小: 83.41MB
- 最后更新: 2024-09-09 08:11:22
- 最新版本: V12.43.4
- 文件格式: apk
- 应用分类:ios-Android 爱情不设限
- 使用语言: 中文
- : 需要联网
- 系统要求: 5.41以上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
爱情不设限